第55期专题文章—2018年3月号
陈佐人教授
(美国西雅图大学副教授)
以下文章是2017神学日感恩崇拜讲章,讲题为「神学的自由」
各位来宾,毕业生,新生,家长与亲人,崇基神学院的学生与教授:
今天是崇基神学院一年一度的神学日,是专为新生,毕业生而办的庆典。首先我要谢谢崇基方永平院长,神学院邢福增院长,关瑞文署理院长,与校董会各校董的邀请,让我今天荣幸成为大会的讲员,与大家分享神学日的喜乐。今天我的讲题是「神学的自由」。为什么是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所以今日经课中约翰福音8章32节中,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大学是寻求知识及自由思想的学府,在大学中的神学院自然是追求神学自由的地方。「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6)
崇基神学组的回忆
谈到神学的自由,我必须提及1980年代在崇基神学组的学习回忆,当时最热门的题目是亚洲神学。那些年头是亚洲本土神学炽热的时代,从小山晃佑到宋泉盛,从韩国的民众到台湾的出头天,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亚洲神学有部份的根源来自中南美洲的解放神学。南美洲解放神学最振奋人心的名言是:解放神学是神学的解放。为什么神学需要解放?因为神学需要从西方的桎梏中被释放出来。神学需要被释放,因为神学作为人对神圣的追寻,有其自身的盲点与偏见。这些包括了在性别,经济,人权,政治,宗教上的歧视与压迫。如果以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典型问题是信耶稣与拜菩萨有何分别,今天华人知识分子的典型提问是基督教神学与意识型态有何不同?
神学教育的解放性(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
解放神学有没有使神学解放呢?当曼德拉从囚犯变成总统(1994-1999)时,南非的解放神学也变成了社会重建的神学。当中南美洲的革命军都当选为执政党时,当韩国的朴正熙与全斗焕倒台后,各地的解放神学都被迫转型。似乎为解放而解放并不能解决人间的万千问题,因为解放是为了自由,为了公义,为了真理。但不是“vice versa”,不能反过来说。
从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古典基督教都致力探讨自由与自由意志。从马丁路德到马丁路德金,现代的基督教都致力争取自由。但基督教是一个带有原罪的传统,究竟路德是促进了自由与现代人权,还是加深了宗教间的冲突与战争?这是今年西方神学界的争论热点之一。以上是历史神学的反思。
接着登场的是圣经科的老师,他们会提醒我们,旧/新约圣经中可能没有现代的自由观。究竟现代的个体自由,人权,私有产权,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在哪里?这是我身处的美国学术界在过去十年的热点讨论之一,特别是英美的法哲学界的专家学者都热烈争论,但结果都是莫衷一是。如果有共识的话,那我们都同意最不可能的来源是柏拉图,但他却同时是西方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奠基人。在美国,我们也同意应不是美国的立国者,因他们大多都拥有奴隶与将女性排拒在独立宣言中。
神学教育的传统性(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dition)
在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没有共识,更无标准答案。崇基神学院作为在公立大学中的神学研究学府,在此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学院的老师为学生提供了批判的思考方法,藉着反思与批判传统,包括旧/新约圣经的传统与教会的神学传统,我们致力去重溯一重生机盎然的活传统,是已逝去的智者的活信念,而不是活者的人的死信念。崇基神学院的老校友一定怀念沈宣仁教授讲Tradition的口音。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死的传统是传统主义,是没有自由的传统;活的传统是生机勃然的“living tradition”。记得某年新学期的第一天,我躲在宿舍午睡。电话突然响起,沈教授打来,说:「陈佐人,你为什么不修我的基督教经典一课?你立即到我们的课室来。」我即连爬带滚地跑到教学楼,小课室内只有五,六位同学,沈老师正在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与上帝之城。沈老师教了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但他不断用的字就是传统─“Tradition”。传统须受批判,传统须要更新,神学才得以自由。
神学教育的大公性(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Ecumenism)
我所说神学的自由,不是自由神学。今天我不会谈及神学的各家各派的问题。崇基神学院是在公立大学中的神学院,像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一样,是以追求神学知识为宗旨,强调对圣经,神学,教会历史,特别是中国教会与香港教会的历史,伦理学等的研究,对整个基督教传统予以批判,重塑与重整。我的老师特雷西(David Tracy),他也曾经到访中文大学,提出了西方基督教的三种空间:学术,教会与社会,分别代表了神学家,教会建制与群体,和社会行动者。我相信近数年来香港神学界的变化是神学学术界的对话对象不再是学界或教会,而是越来越多来自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与对话。神学进入了公共空间,就像路德从威登堡修道院出走,迈进了威登堡大座堂的广场,再进入各城各乡。神学不再是神学院的专利,神学要面对人群,走进社群。
在第二次大战时,西方神学出现了一场庞大的社会运动,全面走进了当时分崩离析的世局。当时抵抗纳粹霸权的代表性人物有改革宗的巴特(Karl Barth),路德宗的潘霍华(DietrichBonhoeffer),他死于纳粹手中。另一位路德宗的大师是田立克(Paul Tillich),国内学者译为蒂利希,加上天主教的彼得森(Erik Peterson),还有犹太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再加上在美国纽约的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他们产生了一幅全面光谱式的反霸思潮。他们批判法西斯主义,再至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再至英美的资本主义。香港需要一种全面的神学思潮,而崇基神学院可以在当中产生催化的作用。崇基的神学反思是在边缘上的反思,是临界的,是越界的。崇基老师中有多位都是田立克的专家,田立克的自传名为《在边界上》(On the Boundary)。我想起了温伟耀教授介绍崇基神学的文章中常有提及田立克,这是一种在边界上的反思,可以结合边界两方的力量。因为剧变中的香港在临界点 (critical point)的压力下,我们需要跨界别的联盟,我们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我们需要宫殿的先知拿单与以赛亚,也需要独立独行,不跟从羊群的阿摩司。但另一方面,边界上的反思是越界的的思维,是要择善固执地反对,不怕提出违背传统,甚至违背常识的主张,因为真正的神学必是自由的。
总结
Boundary九龙塘的著名界限街。今天的香港正在走出这条历史性的界限街的新局面。但前路是那一条街?香港的变化之快之急是教人震惊的。我早上在美国早餐时看见的新闻,除了来自华盛顿与华尔街的新闻,香港事务也常常上了头条新闻。有时候,我上回港飞机前看的港闻,降落时局势已经峰回路转。我们都成了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
面对前境,作为远方的校友,我当然特别关心崇基神学院。我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但相信本人神学的乡音未改。我仍然热爱神学,并在风雨里追赶一种神学的自由。当年在崇基神学组,看见陈法政以武侠论神学,其潇洒,洒脱之反思,正是一种神学自由之思。今天在危机中我们更需要神学之自由,以自由之精神来思想神学,以神学来追寻自由之价值。
我在台湾出生,1967年暴动时全家移民来香港;我在香港长大,自命为典型的「香港仔」;1989年,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至今已差不多三十年。我已不能自命香港人,但我对香港的关心与关注仍在,流行歌的歌词是「情已逝」,但我的情没有逝去。在台湾出生,香港长大,在典型的非宗派教会信主,在崇基吸收了大公背景的神学精神,加上芝加哥的训练,现于一家天主教大学教授更正教神学。这种杂多性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但其根源系来自崇基的边际上思考的神学精神。若要比较后现代的杂多性,香港一定是第一。因此我在对上主祷告中对香港有祈望,更加对崇基神学院,对今天的毕业生有更大的寄望。2002年,我曾经有次参加了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研讨会,莫特曼喜欢在书中间中引用一些中国的例子。他在一本书中引用了中国的成语:骑虎难下。我当时在回应文章中说:今天亚洲神学正在兴起,而这头老虎就是亚洲的神学反思,我们在亚洲与香港的神学工作者,就是要冒险骑上这集不羁的老虎。现今香港正处好坏参半年代的十字路口,我们作神学的学者要有勇气骑上虎背。今天是毕业的日子,我作为师兄来祝贺每一位毕业生:记住下山之后要好好做人,要追求自由,要传扬那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今天是新生奉献的日子,愿你们在未来的日子,在众老师中,能集百家之所长,学有所成,为动荡的香港寻觅真正的平安。我再次谢谢崇基神学院的邀请,谢谢各位同学与家长的光临。但愿上主永不失落的恩典永远与大家同在;也但愿大家以信心来寻求明白,在恩惠中获得救赎,在自由中体会真理,在爱中得到成全。阿们。
讲员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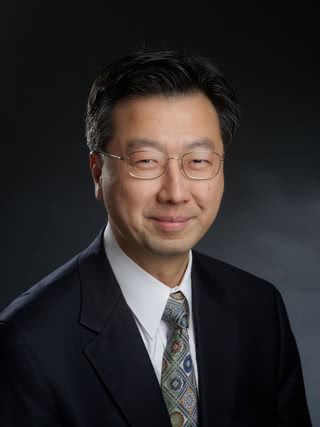
陈佐人博士1989年毕业于本院,获神道学学士,后赴美进修,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自1996年起,任教于美国西雅图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现为副教授,主要任教世界宗教及神学。同时为宾夕凡尼亚州北美归正学院(Chinese Reformed Institute in Pennsylvania)院长。曾任加拿大维真学院访问教授、美国伊利诺州惠敦大学兼任教授及美国芝加哥圣沙威尔大学兼任教授。现为美国宗教研究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美国中国宗教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会员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研究兴趣涉及基督教历史神学、汉语神学、改革宗神学、宗教对话等,曾发表中英学术论文多篇。

